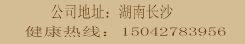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外伤导致视网膜脱落 > 视网膜脱落前兆 > 大家文学微刊年第期大家
当前位置: 外伤导致视网膜脱落 > 视网膜脱落前兆 > 大家文学微刊年第期大家

![]() 当前位置: 外伤导致视网膜脱落 > 视网膜脱落前兆 > 大家文学微刊年第期大家
当前位置: 外伤导致视网膜脱落 > 视网膜脱落前兆 > 大家文学微刊年第期大家
大家葛水平
葛水平,山西沁水县山神凹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小说集《喊山》《裸地》《守望》《地气》《甩鞭》《我望灯》等,散文集《我走我在》《走过时间》《河水带走两岸》等。中篇小说《喊山》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年度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第二届赵树理文学奖,《甩鞭》曾获《中篇小说选刊》年度优秀小说奖,《比风来得早》曾获年度《上海文学》奖,长篇小说《裸地》曾获剑门关文学奖,第五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编剧有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盘龙卧虎高山顶》。
葛水平随笔
从前有那么多牵挂
奇怪的是,事隔多少年我都难以忘怀乡村的舞台,舞台上的一些事,或是由各种关系将我的从前联系在一起的人,或许不曾有过任何生活的记忆,或许因为不曾记得的矛盾,甚至一场单纯的口角,彼此那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们舞台上的妖娆形象。这些记忆是扎了根的,在心里,有时候做什么事情,也不知为什么就感觉那种从前的舞台就非常熟悉地来了。绽开来,仿佛颓败的美好越来越大地澒洞开去。我把他们框在脑子里,很久之后,就想把他们一一画出来,可惜我没有那么多的天赋或秉异。我想,就随性而画吧。
想象一种情景时,脑海中出现的画面不是出自自己的视角,而是像灵魂出窍一般,因为真切地感受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动笔之前,他们只是视觉上一种强烈的刺激带来心尖上的一阵颤抖,墨落下时,黄昏跟随寂寞爬满了我的小屋。一件事情开始之时,我总是怀揣着一个很大的抱负,看着纸上的他们,突然明白,抱负只是暂时被替换了,我还是一个写作者。天边光线的层次穿过云层诚实地映射到我的脸上,我是我,我的画只是内心的一份不舍。不管怎么说,只要写作,只要画画,都可以洗涤我脑海中一些烦恼。
想起童年,乡下的岁月弥漫着戏曲故事,炕围子上的“三娘教子”“苏武牧羊”“水漫金山”,庙墙上的“草船借箭”“游龙戏凤”“钟馗嫁妹”,八步床脸上更是挂着舞台,人人都是描了金的彩面妆,秀气的眉与眼,或者水袖,或者髯口,骨骼间飘逸着秋水、浓艳般的气息。伴随着日子成长,后来又学了戏剧,可惜没有当过舞台上的主角。庆幸更多的日子里站在台子下看戏。正值好年华,那时候,有村就有庙,有庙就有台子,有台子就有戏唱,有戏就会唱才子佳人。舞台上人生命运错落纷纭,连小脚老太都坐着小椅子,拿着茶壶,在场地上激动呢。我看台子上,也看台子下,台子下就像捅了一扁担的马蜂窝,戏没有开场时,人与人相见真是要出尽了风头。台子上,一把杨柳腰,烘托着纤纤身段,款款而行,每一位出场的演员一代一代,永远倾诉不完人间的一腔幽怨。
人这一辈子真是做不了几件事,一件事都做不到头,哪里有头呀!我实在不想轻易忘记从前,它们看似不存在了,等回忆起来的时候却像拉开了的舞台幕布,进入一段历史,民间演绎的历史,让我长时间倘徉在里面。尘世间形形色色的诱惑真多,好在尘世里没有多少东西总是吸引我,惟有戏剧,沉入期间我没有感觉到缺失了什么。比如人生缺失了什么都是缘分,都得感恩。
现在,我手上握着一支羊毫,尽管我只是一个初学者,很难操控我对好的绘画偷窥,很害怕自己喜欢上了别人的东西,很怕被人影响,但是,不影响又能怎样?喜欢的同时又觉得,别人那么画挺好,我喜欢,但是,不是我心里的东西。我想画什么,技艺难以操控我的心力,或者说心力难以操控我的技艺,惟一是,想到我经历过的生活,我感到我自己就不那么贫乏了,甚至可以说难过,有些时候难过是一种幸福。因为,我活不回从前了,可从前还活在我的心里。
文人学画,其实是走一条捷径。即便是诚心画,许多难度大的地方永远过不了关,简单的地方又容易流于油滑,所以画来画去,依旧是文学的声名,始终不能臻于画中妙境。我始终不敢丢掉我的写作,画为余事。
想起张守仁老写汪曾祺,题目叫“最后一位文人作家汪曾祺”,说,汪曾祺的文好、字好、诗好,兼擅丹青,被人称为当代最后一位文人作家,这是因为天资聪颖的他从小就受了书香门第的熏陶。汪曾祺之后,谁还是最后一位文人作家?我自称文人画,有些时候我会脸红。其实,我只是觉得从前还有那么多的牵挂,在精力的游移不定中,文学和画,都是我埋设在廉价快乐下面的陷阱。我为之寻找到了一种貌合神离的辩解,随着日子往前走,有如河床里的淤泥层层加厚,我厚着脸选择了我的生活,而你们给了我一个最高的褒奖“文人画”。我只能说落入任何陷阱都是心甘情愿的。
春天了,风吹着宣纸,飞花凌空掠过,一层景色,一番诗情画意。浪漫而不无虚荣的记忆中,与生活有关,与风霜有关,与情感有关,站在千年文化的凝结点上,需要有和宣纸一样悠远沉静的内敛,我才好去抚慰岁月。
载《文艺报》年4月18日
旧时代里的丰腴又可另解
夏日午后,读一本关于首饰的旧杂志。一篇文章中说胡兰成的女人怀孕了,找张爱玲去倾述,那女人讲到她肚子里的孩子时,脸上有哀婉之色。
张爱玲打开箱子,取出一只金手镯递给那女人。爱,生活的,全都逝去了,寂寞和孤独扑面而来。张爱玲要那女人去当了镯子,取掉那个孩子。那个孩子的出现本就带了一点鬼气。镯子如胡兰成的世井情调,即刻烟消云散。
对胡兰成的认识依赖于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耗尽阳气的男人,嘴角轮廓还算柔和,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张爱玲,我看他时我的嘴角略带嘲讽。一个女人用一只金镯子给他爱过的男人埋单,这个女人容我五花八门去想,始终会想到她的胸襟。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仨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仨字儿,动摇着这个世界建立起来的爱。
这个社会没有一个人敢穿一袭清朝大袍走在大街上,张爱玲敢,她有那份举手投足间的气度。我见张爱玲的照片,她手上戴着的手镯不像是金子的,老照片尽见她的雍容和妩媚,有一段时间我老想她的气质,那腕间戴着的该是什么材质?她的耳环长长短短,倒是都很明朗,每一张照片都可说是配得上经典。
旧杂志里我看见了宋美龄,岁,那张素脸上,两粒翡翠耳扣,被时间的风雨吹得老旧的纸质上看不见成色,富贵人家的阵容还在。左手腕上一圈翡翠玉镯,右手腕上一圈翡翠玉镯,长长的一串翡翠珠子挂在脖子上,我猜她一辈子是喜欢翡翠的。一个女人,年老时脸上已经挂不住胭脂和薄粉了,她依旧画嘴唇涂指甲油,依旧戴环饰。一辈子颠倒众生,迷惑人心,到老都保持着政治界面中贵夫人的格调。欲望对女人的诱惑没有权力支撑时,首饰可以代替并满足一切。
放下杂志时我想起了林徽因。我没见过一张照片上林徽因手腕上有环饰,最多时候是脖子间的那一粒小巧的鸡心长项链,黑裙白衣,她是以书卷味与才女气质行走在民国。从个人化的诗人转型为北京的设计师,当年她拍案大骂吴晗保护北京不利,并勇闯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百试无功下,她痛心疾首地问天:有朝一日,悔之晚矣!尽管有些任性,却恣意得那么可爱。
这个女人,天也妒忌。
我一直无法想像她戴镯子的样子,那么,如果她手上戴了玉镯呢?有人说,首饰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人的生殖区而装饰的。假如是,那一定是吸引,不然怎么会有人会心甘情愿为她孤独老死。
林徽因不需要戴什么首饰,好看的人不戴什么也好看。
说真的,我很喜欢腕间有悦耳的叮当声。有一位朋友,手腕上常戴着沉香珠子,知道他是什么珠子协会的,珠子协会里的人都喜欢收藏什么样的珠子呢?玛瑙?琉璃?玉石?珍珠?金子呢?水珠、泪珠、钢珠算不算?“泪落连珠子”,我想“泪珠子”也该算一种珠宝,因为它有情感。凡是掉泪珠子的人内心都受到了外伤的冲击。其实任何一种珠子都来自于一次意外的伤害。比如珍珠,当海底一只海贝的身体被无意中嵌进一粒沙子的时候,为了保护沙子给身体带来的疼痛,海贝们开始分泌一种液体包裹那粒沙子,时间的最后让它们凝结成一粒珍珠。还比如琥珀,无端的把一只在尘埃中飞行的昆虫胶死在里面。
“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试把临流抖擞看,琉璃珠子泪双滴。”当年看电影《红河谷》,它的主题曲响起,一听到那句“我的眼睛里含着你的泪水”这一句,我便也想落泪珠子。
我有一串元青花包银手链,老瓷黑褐色的斑点上有带点锡光。我一看到它便怀想蒙古帝国控制下的漫漫丝绸之路,到达亚洲的另一端,已经是七百年前的事情了。青花瓷作为中国古瓷中最茁壮的一支,曾经为17、18世纪的欧洲人所迷恋。年七月我去新疆看到艾提尕尔清真寺,我突然明白了青花最初的发展壮大,却是为了响应伊斯兰世界的审美要求。包括后来用的“苏麻离青”就很可能直接来自伊拉克那个至今仍然称萨马拉的地方。艾提尕尔清真寺外墙贴满了青花瓷砖,一个叫香妃的女子葬在里面,听当地的人讲,棺椁里葬有她用过的首饰。
我的那串手链,一些时间里成为我着装的一个“眼”,我穿什么样的衣服,它在腕间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婉约。
旧杂志包含的信息量很多,仔细阅读似乎办刊宗旨就是为了取悦女人。依旧是说女人的配饰,下意识地我看我胸前的三粒“蜻蜓眼”,出土的玻璃料器,也叫琉璃。琉璃被誉为中国五大名器之首(金银、玉翠、琉璃、陶瓷、青铜)、也是佛家七宝之一,到了明代已基本失传,只在传说与神怪小说里有记载,《西游记》中的沙僧就是因为打破一只琉璃盏而被贬下天庭。我用粗麻编了一条绳,那三粒琉璃就坠在我的胸口上。它沉积了历史的华丽,早晨一起床洗漱完毕挂上它,抬眼时便看到世界到处是绚丽的快乐。
和“金”比较,我喜欢“银”,并且一定要老。喜欢老银的色调、质地、做工的样式,因为它传达着一个时代更为丰富的民间气息。
有女子手腕上会戴五六只很素的银镯,它的声响不是翠响,是若即若离。举起手,放下,动作里有银的慰藉,真的很好。
手腕上的银镯,如早晨的树,阳光升起来,隐约间闪亮着银的光,那光如喜动的蜜蜂。
那一年我去德国,在海德堡的老店里,买过一只民国特色的卡扣镯,可以开合,有簧片扣着,两端有银链相系。与漆器手镯同戴在一只腕上有意想不到的特殊美感。在海德堡我还买过一只红金手镯,是一条蛇,两只眼睛是红宝石,蛇头镶嵌绿松石,一头一尾是红金雕花,身子是一种麻,我说不出到底它是麻类的哪一种植物。蛇头下有一行英文,大意是年打造的,为一个女人。天光迅速流尽的冬日傍晚,它弯曲在我的手腕上,我举着一杯红酒,酒精在体内涌动,情绪在流淌中高涨,它从一个欧洲女人的手腕上来到中国,它诞生的那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我的女友说,它的出现有可能是为了纪念他的母亲。首饰天生就是为女人打造的,母亲也是由爱情进化过来的名词,终归是和感情有关。我一直弄不懂。我完全相信,这个世界正发生着比我想象还要出格的事情。
我还有一只藤包银的手镯,上面刻有暗八仙、寿字纹、葵花、盘长、芙蓉等纹饰,分别代表着幸福、长寿、多子、吉祥、富贵。它的空白处有一行小字,上面写了“月下美人来”,另一空白处写了“庆爷”。都是后刻上的。我觉得这几句话有些蹊跷,像是一个女人在偷情。银上的寓意已经明白,再写就是多余。何况那两个字“庆爷”江湖味儿很是十足。我不管它的曾经,我戴着它,我想像我和那个“庆爷”调情,我不给他拒绝感,我只能告诉他,我是你想不到的唯一的一个例外,你已旧去,我还半新。
清代到民国时期精工打造的锁片、项圈之类也是我颈上配饰,如果搭民族风的衣裳走出去也会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老银耳环中隆重的点翠和嵌宝耳坠我也有,一般不戴,我怕丢失。如果要戴,也要选面料柔软、不带蕾丝或网眼的衣服,以防摩擦或勾拉损坏。老首飾全是老银匠手工一点一点打制出來的,可见古代银匠工艺非凡。
我朋友的父亲年轻时是一位小银匠,他说,在过去好的银匠没有三年是出不了师的。好的首饰戴在气质般配的女人身上会叫人眼前一亮,会让我有惴惴不安的心跳。
旧杂志上有文章纪念屈原,诗人把屈原当做自己的祖先。多少富贵荣华,多少功成名就,多少道德文章,多少方略鸿图,一概远去了,可是谁的生命能够嵌入历史呢?那些被欲望绊着脚的享乐不能,历史把屈原抬到了文字的高处。
不想那些沉重的话题了,想五月端阳是一个节日。
想起了端阳节前,生得白里透粉的女孩儿手腕间和脚腕间拴上了五彩丝线,温婉清丽的样子。在黄昏苍茫的院子里蹦蹦跳跳,时间和空间在氤氲之中被分割为两段,小女孩最幸福的年龄时段里一无所知。端阳节好像是给女孩儿过的节日。各种丝线粗粗细细,袖管挽了很高,洗脸玩水都不舍得打湿了。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龄怎么回忆都是一团影子,只记得腕上最早的首饰是母亲给的。“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是女孩儿的另一段开始。苏轼写这首《浣溪沙·端阳》的第二天就是端午节,他写给他心爱的女人朝云。岭南的旧历五月,天气应该是很热了,他的女人要用兰花香草来沐浴,然后用彩线臂缠,以期祛病除灾。
男人是不是每一首诗歌里都要珍藏着自己的情感秘密和生命气息?
端阳节拴五彩丝线,有的地方叫“五彩长命缕”或“五彩续命缕”。“系出五丝命可续”,“五月五日,以五色丝系臂,名长命缕。”后人也称“续命缕”。我小时候戴端午彩线要戴到八月十五,躲过酷夏,在一个有雨的日子我母亲帮我剪下扔进河里。母亲说,五彩丝线可以避邪和防止酷夏五毒近身。我还记得剪下丝线时,我和母亲站在河边,母亲口里念念有词:“叫河刮走吧,刮走近我闺女的邪门歪道。”我看着那旧了的丝线漂在水面上,一个小波浪,一个小波浪翻滚着远去了。河流带走了许多,我一直希望,守着一条河流,过世界上最美的日子,我知道我已不能,每个人都无法逃脱命运的悲剧。
说到悲剧,这本旧杂志上也写到了“杜十娘”,女人一生的财富是她全部心身换得的首饰,她想戴着她的首饰离开那个淫言秽行的下流之地,去寻求清洁雅淡的风流,她不知,世间的“风流”原本都是露水恩情。她只能感叹:“妾腹内有玉,恨郎眼内无珠。”翠羽明珰,瑶簪宝珥,祖母绿、猫儿眼,值钱么?要我看最值钱的是睁着眼看世间百态。我认为,女人自己买首饰某种程度可以助长女性的独立意识和欢喜,男人送女人首饰只能说一时之间可以扩大感情的衍生空间。
有一年去枣庄,去时已是冬天。去看“李宗仁史料馆”。经营史料馆的女人已经逝了,是李宗仁最后一位太太,影星蝴蝶的女儿,叫胡友松。她活着时说:“一生有着太多的迷茫,胸中有着万千沟壑。”影星蝴蝶告诉她:“记住,你只有母亲,没有父亲。”她是蝴蝶和人偷欢而来的。她和李宗仁的婚姻只有两年半。不知道她是否也一样拥有母亲“蝴蝶”的花容月貌?我问那个讲解员,那女孩看着我半天想不出来该如何回答。走到楼上的阳台前她突然回转身说:“她手上一直戴着一个绿色的塑料镯子,因为她的首饰都捐献给了桂林李宗仁官邸,就那个塑料镯子,没有人看得出它的贱来,六十多岁的她戴着,衬托得她贵气逼人。”
女人手上的指环,在古代,戒指是用来区别和记载宫廷女子被皇帝“御幸”的标志。女人“进御君王”时,都要经过女史登记,女史事先向每位宫女发放金指环、银指环各一枚。如果某一宫女左手着银指环时,表示已按排将要与皇帝同欢,而右手着银指环时,表示已与皇帝同欢完毕。如果右手着金指环时,表示正当月事、怀孕之时,应该暂避君王御幸,女史见了就不将其列入名字,起到“禁戒”作用。
项链和手镯就不用多说了,最早则起源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时期所发生的抢婚。在从夫居的制度下,男子往往掠夺其他部落的妇女或在战争中俘获的女子作为妻子。为防止被抢妇女趁战乱或夜间逃走,胜利者往往用一根绳索或树环套住女性的脖子或双手,企图使她们驯服。后来逐渐演变成用金属套住脖子或手。耳环也是驯服女性的“刑具”之一。女人们啊,一路风雨而来,因祸得宠了。生命不可以返回初衷,到后来却点缀得女人风情万种。
看好莱坞大片,会发现好莱坞从来都是混迹着世界上最有型的帅哥,这些人的举手投足包括他们的各种行头通过镜头传递到世界各地,手环、耳环、项链,就是潮流和魅力的标杆。再配上独具个性的发型,一副酷劲十足的眼镜,若隐若现着内敛奢华的袖扣,亦或是标准的六块腹肌……这些面子功课无非是“耍帅装酷”打造出一个型男。只是任何的修饰都不如一款有分量的手表和首饰来得画龙点睛、切中要害。
看强尼·戴普,他可以算是手镯的忠诚粉丝,嬉皮的、西部的、搞怪的……你可以在他手腕上看见各种稀奇古怪又个性十足的手镯、手链。想想看,一个魅力十足的男人,必须是一个懂得在合适的场合借助恰当的装饰表达自我的男人。男人的首饰对接了男人的气质,有时候就是女人的毒药。
杂志的封底是一张老照片,旧的月份牌上穿旗袍的女子,旁边放着一包香烟。和中国的香烟比,我更喜欢西方的雪茄。其实雪茄之于男人,正如首饰之于女人。虽然男人表现魅力不在于肤浅的形式,而在于品味和生活态度。可我总认为雪茄在男人身上的表现,可以让生性浮躁的心有收山之势。作家里边陈忠实抽雪茄。抽抽停停,说说话话。似乎李敬哲也抽,记忆不起来。
对陈忠实想起来较多。主要是因为那张脸,沟壑纵横,似乎是霸河水的波纹深嵌到了脸上,他那张脸很适合画油画。想他头顶扑打脸的尘土,一路走来,在一片金黄色的麦地前疙僦着,嘴里一根长长的汉烟袋,温暖、结实、安泰。可他偏偏抽雪茄。雪茄与他的《白鹿原》的关系,实在容不得我们在阅读中太过傲慢。我和他聊天,雪茄的香气总是在谈话的背景中缭绕,很好闻,有一种促使话说下去的潜移默化功用。那种范儿,不是人人都能抽雪茄。
真正西方现实生活中,能代言雪茄大佬恐怕只有一人,便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历史风云人物,都有自己的嗜好。几乎所有的历史图片中他都是抽着雪茄,因此,雪茄被认为是他的标志性符号。据说,丘吉尔一生中吸过的雪茄的总长度为46公里,吸食雪茄总重量为公斤,是世界上吸食雪茄吉尼斯纪录的保持者。一个首相抽雪茄抽出了自己的牌子,为前卫的世界带来了丰富的人文意义。这些都还是其次了,我欣赏二战期间丘吉尔和一个记者的对话:
记者:“莎士比亚与印度哪个更重要?”
邱吉尔:“宁可失去50个印度,也不能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他之后再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知道:能够征服世界,主宰世界,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拥有文化的精神力量。
我的文学就是民间
一一蒋蓝对话葛水平
蒋蓝:诗人、新散文代表作家。人民文学奖、布老虎散文奖、中国西部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寂寞中的自我指认》《爱与欲望》《复仇之书》《人迹霜语录》《香格里拉精神史》《思想存档》《动物论语》(上下卷)等文学、文化专著30余部。散文、随笔、诗歌、评论入选上百部当代选集。曾任《青年作家》主编,现供职于某报业集团,中国“非马美术馆”文化顾问。(蒋蓝最喜欢诗人佩索阿的一句话:“不能成为什么,但能想象什么,这是真正的御座;不能要求什么,但能欲望什么,这是真正的皇冠。”)
提要
葛水平的小说《喊山》改编成同名电影在今年夏天登陆各大院线,在民间生活的丰厚质地上展现人心中艰巨的大义和宽阔的悲悯,收获了很多好评。葛水平愿意与同乡赵树理一样,“永远站在穷苦人一边,永远站在一无所有的人一边”,坚持写作散发着“山药蛋”特有气息的文字。
嘉宾
葛水平:山西沁水县山神凹人,早年随祖父出山放羊,大抵达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成长。青少年时代学戏,写诗,写戏剧剧本;后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电视剧本,写数来宝;再后来画画。一生追求:多学一门手艺,少求一次人。写有小说作品集《喊山》《裸地》《守望》《地气》《甩鞭》等,散文集有《我走我在》《走过时间》《河水带走两岸》等,小说、散文是谋事,其它作品是谋生。在谋事上对人的把握一直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在谋生上常摆脱一个骗局,进入另一个骗局,随欣慰并懂得都是谎言的世界过于庞大之故。最高获得奖项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爱这个奖,它给了我从来没有梦想过的生存荣誉。
手记
年11月14日
四川省作家协会与绵阳市游仙区举行笔会,邀请作家葛水平参会。作协请我去机场接她。11日深夜,她出现在机场出口,略低头,那一身民国氛围的服饰打扮,在红男绿女之间显得那么特异。这是我第三次与她见面了,每次都是在成都。
成都与葛水平有缘,她前后来过十几回。年4月20日,她在达古冰川采风期间,遭遇雅安芦山地震。急急赶回成都,看着成都市区熙熙攘攘的人流,葛水平沉默好久,她对几位作家说:“我们真是没用啊。现在能为那些人做些什么呢?”
在车上我问她:除了写作,你的生活是怎样构成的?
她幽幽地说话,好像不是在回答我的问题:“我是女性,永远不想改变我柔弱的性别。不想在权力纷争中获取一切,只想不放弃精神享乐。就像我喜欢的文学女子林徽因。她说:外表上看去世界各国妇女的地位高低不等,实际上女人总是低的,气愤也无用,人生不是赌气的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真性情的人,想法总是与众不同。再所以,我微笑。在任何我难过或快乐的时候,我只剩下微笑……”
葛水平并非书虫,她的爱好很广泛,“写作之外我画画,偶尔做做手工活,弹弹古琴,最愿意做的事情是布置家和去乡下发呆。永远是水的流动柔软无骨,却永远地连带着家的快乐。我喜欢写作,写作是家居的日子延续。因此我喜欢居家过日子的平淡。”
第二天是作家阿来的诗集首发式暨朗诵会,葛水平登台朗诵了阿来的一首诗,赢得满堂喝彩。她说,这是她第一次登台朗诵。“我不喜欢那种美声式的朗诵,就像形容词铺张。我的朗诵是民间的……”
繁华与悲凉都应该有人惦念……
好看的基质是文字存在的家
蒋蓝:年,你出版了小说《甩鞭》,甫一面世,一鸣惊人,由此成为你的成名之作,随后创作了《喊山》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甩鞭》的文体创新你认为体现在哪些方面?
葛水平:我认为没有文体的创新,从写作的角度我更注重故事。故事中的人事涉及我的小祖母,我对她有一种无法释怀的爱。童年时过年,她跪在佛龛前,那份颓丧那份对神的埋怨的神情,因为咽炎她的嗓子眼里一直堵着一团棉花,她咳咳咳,扶着桌角站起来时不忘说一句:不长眼睛的神仙啊,从来看不见我给它烧香。也许正是生命的转瞬即逝、命运的动荡不安,神在人世间永远都是离谁都近,离谁都远。神强加给人世间“强人”一只手,那只手由人的意志决定将普通人的命运推向了极致。她渴望神对生命重量尊重,在冰凉的时光中神是她唯一可以仅有的渴望与慰籍,可惜神不长眼睛。守着最美好的山水过着世上苦难的日子,难道这就是命!一条长长的牛皮鞭子,到最后没有叫醒春天,到最后骨架疏散,鞭声干瘦,冻土地上的浮土都没有带起来,何谈气势。鞭声的甩亡预示了家族的败落。我把他们的故事入了文字,因为我知道繁华和悲凉都十分神圣,都应该有人惦念。
蒋蓝:自《甩鞭》发表已13年过去,花城出版社新近推出了《中篇小说金库》,收录了你的中篇小说选集《甩鞭》,有没有修订?具体在哪些方面?
葛水平:能入了花城出版社《中篇小说金库》是我的福气。这套图书是林贤志老师选编。林先生是一位文学大家,我及喜欢他的文字和做人的风格,他不媚俗,干净,不屈服某种政治势力的专横。从他身上我看到了生命高贵的前提是:生命是尊严的。
这次收录《甩鞭》作品没有修订。
蒋蓝:有人说中篇小说很难把握好分寸。理想的中篇小说既应是有好看基质,又应该是有文学意蕴的叙说。好看的小说很多,有意蕴的小说也不难,难在二者兼于一身方为佳作。你的中篇故事性非常强,你对自己的中篇小说如何评价呢?还有何打算?
葛水平:文学作品不是过往的故事苏醒,过往的故事一定有它的现时性,“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好看基质是文字存在的家。好的小说,我以为是作者找到了一个与他的个人气质和所要表达的内容相适应的语言形式,二是审美意义上建立独特的风格。而“基质”,则是在更原始的意义上,保证了人作为历史性的人而存在的可能性。黑人作家莫里森说:“写作是为了作证。”鲁迅、索尔仁尼琴、伯尔、米沃什,还有库切,他们都是为历史作证的作家,也是忠实于人类苦难记忆的作家,因此,也是最受时代欢迎的作家。
我想写作者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评价自己的作品,只管写作,诚实是起点,思想代表深度。我想说,我不是一个幻想未来的作者,我只是不想放弃过去的错误、罪恶、缺陷,以及一切过往日子里的苦难。我会一直这样写下去,尽自己的能力去亲近普通人的命运。
好作品定有来自民间的声音
蒋蓝:有论者认为,你的文学写作与赵树理作品中都散发着“山药蛋”特有的气息。你对此如何评价?
葛水平:赵树理是一个高度,后来者无法逾越,也无法模仿。也许我们同一出生地:山西沁水县。都知道,出生地是重要的,惟有生活才能涵养生命。无论一个作家具有何等非凡的想象力和虚构能力,出生并成长中经历的事实和经验对他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方言、乡亲、习俗,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山药蛋气息?洛尔卡曾经表示过:“在这个世界上,我一向并将永远站在穷苦人一边,永远站在一无所有的人一边,站在连空洞无物的安宁都没有的人一边。”如果我与赵树理先生同是站在洛尔卡所说的一边,评论界用在荒年里养穷苦人命的山药蛋来冠名,我想我是喜欢的。
桑塔格认为,土星气质对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殉道者是一种合适的气质。也只有这样气质的写作者,思考的头脑才更为有力,更有创造性。其实,很多写作者都存有故乡情结,好的作品一定可以感同身受故事里人事的疼痛。好的作品,一定可以听见来自民间的声音,也只有民间是生动的。
蒋蓝:年8月,根据你的小说《喊山》拍摄的同名电影,正式登陆各大院线。由杨子执导、郎月婷、王紫逸、成泰燊、于皑磊主演的《喊·山》,作为一部良心之作,成为近期最为期待的电影之一。在近半月的全国路演看片中不断收获好评,得到了影迷的热情支持。你认为电影达到了你心中的构想吗?
葛水平:作为海归的80后导演杨子能倾情拍摄这样一部良心之作电影,他是成功的。因为他不知道北方的农村和北方的农民。一要坚守作品的原本样子,二要考虑市场,他能够坚持拍摄下来也算是不容易。从我自己的作品出发,有些地方我是不喜欢的,小的细节不说,大的方面就有,岸山坪人要赶走哑巴红霞,这在太行山的乡间,只有对外来人口的呵护,少有对外来人的驱逐。
蒋蓝:当代有很多打着“民间”旗号行走江湖与t型台的艺人、诗人。但是“民间”恰恰是你文学的底色,可否描述你心目中的“民间”?
葛水平:我的民间可能已经老去。老去时我竟然找不到理由,它的老去不像一场战争或者一次政治运动那样声势浩大,它在你视野中,在你转身之间它就老了。老去的乡村里居住的乡亲,他们的眼睛里射出了慌乱,长了多年的果木树上的果实,他们甚至都来不及瞭一眼。慌乱中他们撂下一句话:“往昔等不得熟透就被娃娃糟害了。眼下你寻得见遭害它的人?”
我的民间不是这样子。
所有的情爱都深埋在泥土里等待发芽。阳光架在屋顶的瓦坡上,泥地上有成群结队的鸡,山坡上有成群结队的羊,上地或者下地有成群结队的人。成群结队的风跑过来捣乱,有妖娆的声音传过来:躲开风啊,小心被风呛住弄眯了眼。风趁机挑逗她的嗓音,祖母说:这个女人总喜欢在风头上戏弄一些是非。我在他们的名字中间生活,他们深谙人间烟火,又具有对日常恩怨的简单消解,面对生活和生活之外的事情,他们更在乎活着,更在乎收获时多物种的丰收。在乡村你可以随时感觉到人的呼吸,田野上掠过的秋风中伴随着狗叫声,只是我已经听不见凌乱做迷藏的脚步声了。
把民间变得轻贱卑微的历史,必定是一段走失了人性的历史。
乡土、行走与历史踪迹
蒋蓝:散文、随笔是你小说创作之外的重要体裁,你的散文里不仅展示了对乡土情怀的坚守,更表现出难得的对历史文化的深刻反思与对生命意识的高扬。这在女作家里并不多见!
对当代女性散文写作有什么看法?
葛水平:散文同小说一样都应该致力于人性美的发掘。我不太喜欢微小叙事的文字,充满一种伪小资般的满足感。就像一位西方诗人所形容的那样,“似乎声音都贴在自己的脸颊上”。出于自己爱好,我喜欢某一层面作较长驻留的散文家,因为爱是需要时间的,我在她们的时间中阅读文字感觉的触须,情感的波纹,思想的褶子,并且和她们笔下的人物和事物,亲切有如重逢的相视。我的阅读才是快乐的。
蒋蓝:年10月,你开始沿沁河行走,从沁河源头的沁源县,历经沁水、阳城、泽州等地,一直到汇入黄河处的武陟县,断断续续,历时一年多,深刻地体验了沁河流域的历史、文化、生态及乡村的风土民情,写出散文集《河水带走两岸》。这一情形,与我写《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颇为近似。请谈谈你对文学田野考察的心得……
葛水平:你的散文《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我阅读过,写得好。作品在坐实人物的历史时空坐标之余,更为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iwangmotuoluo.com/stqz/177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