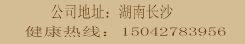年2月23日,早上七时,零下1摄氏度,霾转多云。吸入鼻腔的空气凉而干涩,冬末的北京,寒意尚未消散。
我直挺挺地站着,把冻得有些僵硬的双手缩进袖口,眼前一片黑暗。有人说着话,有人在前面拍打自己的身体。脚步声从各个方向传过来,像分好了声部的鼓点一样敲在地面上。一个一个的行人从我右手边快速掠过,带走一阵风。
“开跑啦开跑啦”!我应声向前挪动了步子。
在黑暗中奔跑,我能抓住的只有一根绳子。
1.1开始的每一步都很艰难,每一步我都只敢把脚往前伸出一点点,脚底下和心里都空落落的。
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不知道前面的人离我有多远,不知道我到底跑在什么地方。我怕摔倒,怕撞上人,怕自己偏离了方向,怕前面有坎、路边有沟。我有点失去平衡,我想扶着一点什么。
我把脚步放得更慢,身体不断靠向绳子的另一端——我的助盲跑步志愿者Jerry。
Jerry跑在我的左边,我们分别抓着助盲绳的两端,中间稍有些距离。助盲绳可以让我不至摔倒,却不能消除我内心一丝一毫的恐惧。我不断地向左边靠,当左臂触碰到Jerry胳膊的时候,我才终于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支点。
Jerry感受到了我的紧张:“要不然我们停下来走走吧。”
“没事,我们还是继续跑吧。”刚刚开始跑没多远,我不想放弃。与心里的恐惧一比,“面子”明显占了上风。
“好,那我们稍微快一点,跑跑可能就适应了。”Jerry说完,绳子便开始收紧向前,我硬着头皮迈大了步子跟上她。
“前面我们要先右转再左转。”Jerry提醒我之后,我开始有意识的往右边跑一些,不过要往右边跑多少我不知道怎么把握,全凭着自己感觉来。绳子一下松一下紧,我与Jerry的距离时近时远,在一通拉拉扯扯之后,右转的弯总算是转了过去。左转显得比右转轻松得多,Jerry比我靠前一点先转弯,她用绳子一带,我就顺势往左边跑过去了,我爱左转。
“我们马上要上桥了,有一点点坡度。”Jerry边跑边告诉我前面的路况。
刚刚蹬了两步就开始下坡,踩得深一下浅一下的双脚告诉我这座桥比我想象中短。
“您已经跑了1公里,耗时7分钟22秒。”,手机里传来跑步APP报时的男声。
七分多钟的时间里,即使开跑时担心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发生,我脑海里紧绷的弦和攥着绳子的手还是一刻都不肯放松下来。Jerry就跑在我旁边,可在奔跑中我能真真切切抓住的还是只有助盲绳。
我命不由我,我命由绳。失去对自己的掌控,把自己交给身边的人,这是我恐惧最大的来源,也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
其实我不是盲人,我只是戴上眼罩,体验了一次盲人在黑暗中奔跑的感觉。
1.2奥森(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是北京最负盛名的跑步圣地之一。这里记录着“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也成为了何亚君助盲团视障跑者们在北京最熟悉的地方。自年五月成立至今,每周三和周六的早上七点,盲友(视障跑者)和助盲志愿者们都会在这里训练。即便是寒冷的冬天,来参加例跑的也有百余人。我和Jerry就跑在助盲团三队的队尾,跑在我们前面的还有十几对盲友和志愿者组合。
跑过第一公里之后,脚下的路平顺了很多。耳朵里全是“啪嗒,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即使没有人喊“一二一”的口号,队伍的脚步声也非常整齐。我把脚步踩进节奏里,好像也为这段“演奏”贡献了一部分。
“今天开路的是阿振,配速的杨言和周姐。”秦姐的声音从前面传过来。
“秦姐”是大家对三队队长秦毅的称呼。因为配速适中,三队的人越来越多,队伍也越来越长。秦毅边跑边给大家做着介绍,争取让每个人都能对上号。
从年助盲团成立之初,秦毅就在助盲团做志愿者。去年九月,助盲团开始根据跑步的速度和距离分队训练,秦毅便成为了三队的“大家长”。设定训练计划、做例跑总结、给报名的盲友和志愿者配对、协调和沟通,秦毅用了很多精力。三队盲友的脾气秉性、训练状态,秦毅大多都心里有数。
一年前,秦毅从北京搬到了燕郊生活。每周六来助盲,秦毅需要花掉三个小时,转乘三种交通工具。早上四点钟起床,洗漱完毕之后出门,骑自行车到公交站赶四点五十的早班车,公交车会在六点钟到达国贸。从国贸到奥森,秦毅还需要再坐14站地铁。和盲友们无话不说的秦姐,一年来一直守着这个秘密。助盲这件事是自己喜欢,她怕盲友们知道了以后心里有负担。
“阿振,杨言,周姐”秦姐起了个头。
“加油!”我也鼓足了劲跟大家一起喊。
“第二排的是楠和粘川,第三排的是芹和明月。”
“楠,川,芹,月”,“加油!”
喊了几声之后,我反倒觉得舒服了很多。注意力被秦姐和大家喊口号的声音转移,我开始对眼前的这片黑暗没有那么抵触,试着把自己放松下来感受它。
“秦姐看着!”跑在前面的志愿者突然喊了一声。
汽车从我们左边驶过,队伍还在继续向前奔跑,幸好没事。
1.3对着眼前的一片漆黑跑步是有些枯燥的。
“树枝上的叶子还没长出来,一排排光秃秃的树错落有致参差不齐的分布着......哈哈哈。”Jerry给我讲起了路边的景色,说到一半有些词穷便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们经常会给盲友说说这些,春天的时候花刚开起来特别好看,夏天的时候就是满眼的绿色,秋天的时候叶子变黄,可是冬天我就不知道怎么说。”
跑了十几分钟,脚下越跑越开,我身上也越来越有热乎气,只是左手一直紧抓着绳子不敢动,变得有些僵硬。Jerry让我把左臂也自然地摆起来,她的摆臂会保持和我相反的方向。我开始配合着脚步摆动左臂,感受绳子在我和Jerry之间悠荡。不和这根绳子对着干之后我的确觉得轻松了一些。
Jerry第一次助盲时并没有现在带我跑步这样从容。“我一开始对盲友特别小心,不只是跑步时,也包括言辞上,不敢问太多关于他们眼睛或生活的问题,怕触及到他们痛点。”
年初的一次马拉松比赛上,Jerry看到了何亚君助盲团的盲友和志愿者,完赛之后就她就马上上网找到了助盲团的联系方式。做了几次志愿者以后,Jerry发现盲友们比她想象中要坚强得多。他们内向,他们健谈,他们也一样有说有笑、他们也一样爱美。
(图源:纪录短片《你是我的眼》)
“团长和我说,他们最希望的是我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待他们。”和团长接触多了,Jerry常被启发,也常被震撼。
团长何亚君也是一名盲人。由于高烧导致视网膜脱落,何亚君在十四岁那年彻底失去了视力。22岁的时候,他从四川老家来到北京,开始学习推拿按摩。
转眼十几年过去,何亚君已经在北京开起了自己的按摩店,结婚、生子,在北京跑步圈也颇有名气。
何亚君开始跑步源于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朋友石瑜的带领下跑了七公里,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从10公里到15公里再到半马、全马,从国内的马拉松赛场跑到巴塞罗那的马拉松赛场,何亚君实现了很多个“不可能”。感受到跑步带来的快乐之后,何亚君有了帮助其他盲人一起运动的想法。于是在跑友的帮助下,何亚君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益助盲跑步团,快四年下来,前前后后加入的志愿者和盲友有千余人。
(右一为何亚军)
从马甸东路的按摩店出发到奥森参加例跑,何亚君要先步行多米走到健德门地铁站。有一年冬天,何亚君自己从店里出发去跑步。大风让他迷失了方向,车在哪里、人在哪里都变得难以感知,怎么走都找不到地铁口。周六早上的马路上没有人,他也找不到人问路,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走了40分钟以后,终于碰到了一个骑三轮车的人带他到了地铁站。经历了这次迷路以后,何亚君没放弃跑步,也没麻烦别人来接送。只是之后每次再走这段路的时候,他都默默在心里数着数。一年以后,走多少步,往哪边转弯,全都记在了他心里。
这段迷路的故事不仅震惊了Jerry,也成了很多盲友独自出行到奥森来参加例跑的动力,团里很多全盲盲友现在都是自己坐地铁从工作的按摩店来奥森跑步。
征服过五岳,在峨眉山“看”过日出,在黄山“见”过云海。与大部分视力正常的人相比,何亚君“看”过的景色一点都不少,一点也不逊色。在跑步之外,何亚君又给自己定下了攀登座名山大川的目标。
“那天有零下十几度,最后八公里我实在力不从心了,团长就一直鼓励我,最后到终点的时候我都要感动哭了,要不是团长在我肯定早就放弃了。”
Jerry和我说起上个月和团长一起参加的野鸭湖马拉松,与其说是她带团长,不如说是团长带她跑到了终点。助盲这件事情,看起来是我拉着你,其实你也一直拉着我。
“团长真的是个超级赞的团长。”
1.4“前面有一个大上坡,调整一下呼吸。”Jerry提醒着我。
我深呼吸了两次,做好准备。
我们的队伍并没有因为上坡而降速,跑了几步之后我就感受到了小腿的一阵酸胀,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还没完啊?”我边大口喘着气边问Jerry。
“快了快了,还有不到米。”Jerry回答道。
米还好,我加快了摆臂带着自己往上跑。不过这个坡实在太陡太长,我实在跑不动了,全靠Jerry继续拉着我。“好了已经到平地了。”Jerry告诉我,我却已经没有了和Jerry说话的力气。
我对这个上坡印象很深,不仅仅是因为它难跑。第一次来参加例跑的时候我在四队,在志愿者王新锋的帮助下,我带全盲的盲友广乐跑了一段路。
第一次做志愿者的我没有经验,和广乐跑步的节奏总是对不上,王新锋就告诉我该怎么配合广乐的脚步调整步伐和摆臂。遇到了特殊的路况,王新锋会提前提醒广乐,这是两个人搭档了半年的默契。
王新锋和广乐第一次搭档是在去年秋天的第七届盲人长跑节。长跑节几天前,广乐感冒了。感冒跑步很危险,但广乐不想错过这次机会,王新锋就只好带着广乐慢慢跑,一路上拉着他不让他跑太快。
问起那次感冒还坚持跑的原因,广乐说:“最起码我要向德意志品格学习。”广乐从04年开始“看”足球,各支劲旅中最钟爱德国队。除了欣赏德国队全攻全守、高位逼抢的战术,一场场比赛中从不言败、身陷绝境绝地反击的“战车”精神也影响了广乐面对生活的态度。
我一路带着广乐跑到了这个大上坡,可是跑到一半我的小腿就开始抽筋。怕影响到广乐,我把助盲绳交回到了王新锋手里,这个大上坡也就成了我第一次助盲之旅结束的地方。
好在这次没有在这里败下阵来,小腿只是有些酸胀,我还能继续往前跑。
“何亚君三队”,“加油!”
“何亚君三队”,“加油!”
刚刚跑过的上坡让大家都很累,秦姐带着大家加油打气,我喊得断断续续,跑了一会儿才把胸口的这口气喘匀。Jerry把绳子往左边拉了一下,带着我快跑了几步,原来是前面的盲友有些不舒服,从队伍中下去调整了。
空气里传来一股水腥味,Jerry告诉我左边有一片湿地,眼前的一片漆黑里开始透过一团黄色的光。
“是太阳出来了吗。”我问Jerry。
“你能看到吗?太阳升起来了,现在在我们左前方。”Jerry对我突如其来的光感显得有些兴奋。
我一边跑,这团黄色的光一边在左眼前跳动,阳光照得满脸都暖洋洋的。或许我今天看到的这幅跳动的日出景色,就和有光感的盲友们每次例跑看到的日出一样,阳光洒在树枝上一定也很美。
“久哥,大胡子,帅不帅”,“帅!”
秦姐带着大家一喊,我就知道久哥和大胡子肯定正在我们周围某个地方,手举“大炮筒”对着我们按下快门。Jerry告诉我摄影师在左边,我却一瞬间不知道该看向哪里、做什么手势,只顾着傻笑,拍照的时候笑总是没错的。
久哥和大胡子都是助盲团的志愿摄影师,只要有时间就会来给大家拍照。久哥爱好摄影,平时常拿着相机各处采风。年顺义半马,久哥拍下了志愿者和盲友手里拉着的绳子,从那以后,他也跟这根绳子结了缘。
每次拍完了例跑的大合照,各队开始出发跑步,久哥和大胡子就开始在南园各处找好“据点”等着大家经过。拍完之后选片、修图,再把照片都发到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iwangmotuoluo.com/styy/153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