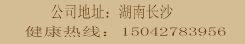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外伤导致视网膜脱落 > 视网膜脱落征兆 > 今晚的头条,我们留给阿璞
当前位置: 外伤导致视网膜脱落 > 视网膜脱落征兆 > 今晚的头条,我们留给阿璞

![]() 当前位置: 外伤导致视网膜脱落 > 视网膜脱落征兆 > 今晚的头条,我们留给阿璞
当前位置: 外伤导致视网膜脱落 > 视网膜脱落征兆 > 今晚的头条,我们留给阿璞
作者
南风窗记者肖瑶
眼前是熟悉的淡绿色墙壁和橘黄色窗帘,迟暮从阳台涌进来,屋子里挤满十几个人,显得有些闷热,天花板上两只吊扇噗簌簌地打转,倒更像在发散一股薄薄的热量。
众人安静下来后,小型音响里开始按顺序播放阿璞遗嘱里提到的古典乐曲目。第一首是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节律震撼,恢弘,继而沉寂,克制,像屋内所有人低沉而平静的情绪。
这是年7月12日晚,阿璞离开这个世界的第20天。不久前,立夏后第一天的清晨,43岁的艺术家陈元璞突发中风,抢救无效去世。
也是在这一天,阿璞年近古稀的父母才挨个通知完亲朋们阿璞的死讯,“身体差了,不敢一下子处理这么多问候,只能分批一个个通知。”阿璞和他收集的近张古典音乐唱片和本相关书籍
这个小型音乐会的与会者都是阿璞生前的亲友,众人纷纷低头,有人抹起了泪,他们不是没有预想过这一天的到来,只是每个人都没曾想过它来得如此快,如此猝不及防。
阿璞爱笑,爱与人交谈,爱在第一时间给别人的朋友圈点赞,但22号那天上午,大家都没有收到他的点赞。
第一个发现不对劲的人是他的师弟和挚友,视障少年王子安,阿璞最爱在子安分享的歌曲底下评论。22号夏至这天,王子安在朋友圈分享了一张歌单,是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船上乐队演奏的音乐。大半天过去了,他没等到阿璞哥哥的点赞。
接着,噩耗传来。
阿璞创作的部分作品
阿璞曾表达过,希望离开世界的时候“不用悲伤,要用欢乐的方式”,遵随其愿,医院病床前用手机播放了贝多芬的《欢乐颂》,声音不大,怕吵到其他病人。
“元璞”这个名字是爷爷取的,在《辞海》里的意思是“第一块没有任何杂质,没经过任何雕琢的原始玉,质朴。”
“阿璞”则是广东本地的叫法,充满亲切感,乍一听像在唤一个孩子,怎么也长不大。
但阿璞一直走在所有人前面。子安这么说,恩师关小蕾这么说,与阿璞拥抱过的人几乎都这么说。
阿璞的“幸福”一生
年春天,阿璞出生时就注定比别的孩子都更晚融入这个世界:他睁不开眼,不会吮吸,直到两岁才学会走路。逐渐长大后也体弱多病,肺炎、哮喘……被医院跑。
直到6岁,阿璞被诊断为轻度智力障碍与神经发育不完全,即俗称的“弱智”。
为了照顾阿璞,妈妈从教师转岗为普通职员,她欲哭无泪:学校里的孩子我不教,有别人会去教。我自己的孩子不管,就没人管了。
从3岁开始,阿璞展露出超常的绘画天赋。行动不利索,不喜欢蹦蹦跳跳,独爱涂鸦,一画就是七八个小时。
三岁的阿璞在墙上画画
坎坷多舛的人生道路,注定要被绘画改写。
年,刚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的年轻老师关小蕾进入广州市少年宫任职,几个月后,一位母亲将儿子带到她的面前。
关小蕾见到的是一个瘦弱、话多但充满灵气的可爱男孩,她让他作画,不一会儿,她看到了一幅至今难忘、后来也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画:画面上有鲨鱼和鳄鱼,生动、立体,充满着极具想象力的空间层次感。
阿璞创作的《春之祭》
关小蕾深感震撼:这个男孩看世界的眼光,远不同于一般孩子。
这幅画正出自8岁的阿璞之手,这之前,他因为不按要求作画三次报考少年宫不中。但在关小蕾眼里,阿璞已无师自通,她破格收下这个智力不足却有着非凡绘画天份的孩子,阿璞成为广州市少年宫的第一个特殊儿童学员,开始了12年的绘画学习。
这场看似偶然的师生初遇,不仅改变了他们彼此的命运,更给整个广州,甚至全国的特殊儿童都带来一次重生机会。
阿璞创作的《日出》
年,在关小蕾的提倡下,广州市少年宫开设了全国第一个“特殊儿童美术实验班”,免费接收包括自闭症、脑瘫和唐氏在内的孩子,开始了特殊儿童艺术教育的探索之路。
全国首个校外特殊儿童绘画实验班也因阿璞而起。年,广州市第二少年宫正式成立特殊教育部门,开始了面向特殊孩子的正式教育,目前每年为特殊儿童提供个多免费学位,设置60多门课程。
长大后的阿璞留在少年宫教书,把自己当年获得的天眷传递下去。一教就是十多年。
他带领孩子们画恐龙,画小鸟,一如自己当年,用生命去感受生命,然后选择一种最具有力度和震撼力的形式呈现出来。
阿璞在少年宫辅导孩子
但身体的厄运却没有终止。21岁,阿璞被诊断为精神分裂,大量服药治疗,几乎沉睡了三年。
28岁,他写道:我这个年龄是青春男女谈婚论嫁的年龄,我的问题比健康正常人更有难度。我把对优秀女性的美好感觉转化为艺术创作的动力,这是人类的美好境界。
阿璞认为他所有的自信来源于福楼拜的一句话:“艺术广大之极,足以占有一个人。”
这让人想起塔可夫斯基说:只有当人们足够渴望精神和理想时,艺术才会产生,才会存活。这种渴望让人们被艺术深深吸引。
年,刚三十而立的阿璞因过度劳累诱发了“脊椎良性海绵状血管瘤”破裂,并流血压迫脊椎神经而导致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生活不再能自理,只得靠导尿管排尿。
这是他离死神最近的一次。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卧床半年,一年多针灸,坐轮椅两年,他才慢慢恢复,艰难地做着康复锻炼,几乎不能再绘画。
37岁,阿璞又忽然被诊断出来“中风”,行动愈加不便,要用助步器,随时需要外出“导尿”。
到这里,阿璞给身边几乎所有人留下的印象,也“总是笑嘻嘻的”,虽然饱受病痛之苦,但似乎烦恼,忧愁,甚至死亡,也永远不会找上他。
“无音之乐”
年,阿璞21岁,他的首部个人画册《无音之乐》出版了。
这是阿璞“用音乐作画”的一次集合,黑白线条将他喜爱的马勒、柴可夫斯基、瓦格纳等音乐家的作品,用独特、灵动的方式铺展在画面上,著名画家刘仁毅点评道“阿璞有灵耳,妙笔传大声”。
《无音之乐》里的《莫扎特—魔笛之第1章》
“无音之乐”这个词很容易让人想到《道德经》里另一个汉语成语:大音希声。“大方无隅,大器免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表达对自然纯璞、净洁形态的崇尚和尊重,对人类原初状态的回归。
阿璞是在九岁起开始“画音乐”的。
年的一天,少年宫美术培训部的郭伟新放了一首轻音乐给阿璞听,并告诉他:听到什么,就画下来。
听着音乐,一只又一只鸟在阿璞笔下生动起来,朝着远处连绵的险山飞去……郭伟新一辈子也忘不掉这张画——《群鸟过险山》。
也是在这时,阿璞开始了在音乐与绘画中体悟生命的新旅途。
从交响乐里汲取创作灵感,他有着一套独特的解码:一段旋律主题可以绘成一个画面。比如十九世纪前的音乐呈现叙事性的画面,现代性的交响乐则更加符号化。对古典交响乐的个性化体验,让他的画面呈现出有秩序发展的隐约的时间线。
阿璞创作的部分马勒古典音乐画作品
短暂一生内,阿璞共围绕音乐创作了多幅作品,其中多幅是古典音乐。“那些经典的古典音乐是大师们用命写出来的,而我的古典音乐绘画,也是用命画出来的。”阿璞在自述里说。
年,里赫特、索尔第、切里比达克三位音乐大师相继去世,对阿璞的精神造成了极大刺激。悲痛瞬间吞噬了他,他愈加没日没夜地拼命画画。
阿璞创作的部分马勒古典音乐画作品
过度的劳累和情绪的持续亢奋,导致他很快产生幻听,继而发病,那次,他在学校里见到爸妈,目光呆滞、胡言乱语,不认识父母,只时不时学小狗小猫叫。
在35岁那年,阿璞写下了自己的音乐遗嘱。遗嘱最后有一段说明:“死之并不可怕,应该顺应它,学习它;时间到都顺了,不要惧怕它;死亡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一扇门。”
他总是笑着走在前面
子安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阿璞哥哥那天:年5月17日,14岁的子安作为少年宫优秀学员代表,去北京参加央视星光大道举办的全国助残日活动。在路上,他遇到了同行的阿璞。
子安起初是被音乐吸引的。他察觉到一个人随身带着一只音响,正播放古典交响曲。两人就音乐聊了起来,竟一口气谈了两个小时。子安感到不可思议:世界上怎么会如此狂爱古典音乐的人?怎么会有比我还“啰嗦”的人?
阿璞创作的《柴可夫斯基:“悲怆”交响曲之第一乐章》
不论和谁谈起古典乐,阿璞的话都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滔滔不绝。从巴赫到瓦格纳,从文学到哲学,子安惊诧地想,阿璞的脑子里几乎装着整个世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不仅是音乐。
两个相差22岁的古典乐发烧友,就此结下了忘年之交。
年,王子安刚出生时被检查出视网膜脱落,只拥有微弱光感,人生从一开始就陷入黑暗。5岁时,子安开始接触钢琴,忽然在音乐里找到一种狂热和振奋。“看不见怎么了?我的人生仍然充满可能。”他对自己说。
小时候的子安和阿璞
但阿璞给子安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一个精神榜样。因为音乐,两人之间有了一种默契,阿璞不定期给子安分享歌曲和自己的评价感言,引导子安在正确的音乐道路上走下去。
偶尔也爆发争执。不仅是艺术,还包括许多共同缠绕着两人的困惑。比如,一个问题至今还未辩出你我:人类将会走向何方?
阿璞告诉子安,人类极有可能会灭亡。子安却不以为然,他坚信,只要优秀的文化艺术得以传承,人类就可以另一种形式永续存在下去。
子安(左),阿璞和关小蕾老师(右)
凭着出色的中提琴演奏,18岁这年,子安被世界知名音乐学府英国伯明翰音乐学院录取,他开始在这条崎岖的道路上看到愈渐明朗的光。
不论是少年宫,是阿璞,是那些一直在引路的教育工作者,总有一种精神持续存在着,近似于黑暗里的光亮,打碎后的重建,绝望中的希望,冷漠里的暖意,这个快速迭代世界里的温柔缓慢……
就像广州大学动画艺术系教授周鲒总结的:在没有光明的地方,黑暗也是一盏灯。
一条道走到天亮
第一次与阿璞对话,周鲒便感到“惊恐”:眼前这个传说中“弱智”的人,如此坚决、铿锵、口若悬河地讲着未曾看到过、去到过的异国他乡和陈年旧事。
这几年,阿璞身体越发不便,有时正聊着哲学、美术到兴头上,他会忽然停下来说,“我去导个尿”先,然后拿着尿管去厕所,房间里仍然放着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厕所里传出水流声,周鲒就听见阿璞大叫,“快听——开始杀人了,杀人了……”
阿璞创作的《杀人·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三交响曲》
每到这种时候周鲒就忽然觉得,在这一间房里住着的不仅是阿璞,还有巴赫,莫扎特与马勒。
有一天,阿璞告诉周鲒,他打算把整个西方音乐史画完,此时,他已经画了多幅古典音乐绘画。
认识阿璞之前,古典音乐之于周鲒,只是偶尔的耳朵调剂,莫扎特和柴可夫斯基并没有真正“插入”他。
年,周鲒与阿璞共同出版了一本《古典音乐对谈录》,书中选了七首阿璞最喜爱的交响乐,用图文方式记载了阿璞对于音乐的感觉,也通过对话呈现了众多音乐的社会历史、音乐大师的心灵轨迹
慢慢地,他从阿璞身上感受到一种催促自己去反思的力量,去思考超出艺术以外的东西,关于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关于人类的终极价值。
与阿璞的十年交情,逼着身为教育工作者的周鲒反思:“今天我们的教育都强调‘起跑线’,强调竞争、努力,‘成功’两个字成了全社会的魔咒,阿璞的故事恰好相反,他‘输在了起跑线’上,他人生的每个环节都和大家格格不入,但当他离开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在赞美他,为什么?”
周鲒(左)与阿璞(右)
周鲒想起今天有个流行词“前浪”和“后浪”,阿璞是什么“浪”?“他是被浪卷走的泡沫,被浪淹死的无辜者,但今天,他是‘精卫填海’。”
到今天,他似乎还常恍惚看见那个常穿红色上衣、体型瘦弱的阿璞,缓慢而坚定地,一步一步走在从西华路到少年宫的天桥上。看着阿璞的背影,周鲒就想到尼采的一句话: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不是要复制“阿璞”
几十年内,无数教育工作者投入特殊儿童的艺术指导,无尽精神力量的推动下,这条路逐渐光明和开拓。
自年开创特殊教育先河后,关小蕾一直致力于“融合教育”。
“融合教育”的理念源自西方,指将身心障碍学生和普通学生放在同个学习环境,强调平等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iwangmotuoluo.com/stzz/16771.html